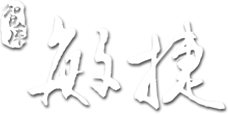如果你看过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的网球比赛录像的话,会发现那是一个和当下完全不同的技术时代。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正反手技术,网前截击,都遵循着“推”球的原理。也就是,要在球和拍面之间保持一个适当的停留时间。
大概是80年代后期,球拍的制造工艺有了飞跃,新型的科技材料被运用其中,球员可以更自如地释放着自己地力量,也就是绝对力量开始逐渐取代击球技巧。为了让比赛更具观赏性,球拍地拍面也越来越大,比如张德培就使用了史无前例107拍面。
随着球拍科技改变的,还有击球技巧。在我学习网球的时候,正是桑普拉斯代表的东方式握拍退潮,阿加西代表的半西方式握拍成为主流,休伊特和罗迪克代表的西方式和超西方式开始登场的多元时代。那是处于世纪之交,老天王桑普拉斯和新天王费德勒的权杖交接期。
从费德勒统治网坛开始,西方式握拍彻底成为了主流,虽然费德勒本人是半西方式。对于西方式握拍而言,球员摒弃了经典的“推”球原理,而是更多借助自身的爆发力猛力抽球。因为我算是经历了两个技术时代,对其中的差别感受颇深。感觉之前教练教的技术动作被完全颠覆,直到我站在球场上,发现自己就是一个老古董。
而球拍的制作技术也是发展地非常迅猛,各种科技元素被掺杂在一起,以至于每一年都会有新品出现。这和桑普拉斯时代一款球拍畅销10几年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球拍科技改变了,击球动作改变了,甚至规则也发生了变化,比如鹰眼的应用和选手的主动叫停。但是有一点却是从网球运动发展至今,都没有发生变化的,那就是这项运动的精髓——用脚步去寻找击球点。
真正懂网球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网球是一项步伐运动,眼睛和手臂不过是辅助材料,真正体现一个人天赋的是他是否可以用脚步来锁定身体和球之间的最佳距离。我记得纳达尔有个很牛逼的实验,他被蒙住了双眼,仅仅凭借感觉,就能做出正常的底线抽球。这是因为他知道只要双脚不被束缚,他总能想办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你看各个时代的网球训练教程,步伐训练都是最基本的。这是从来没有变化过的。
只要事物的本质不发生变化,所有形态上的变化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本质。对于网球而言,更加强调自身力量的击球技术是为了更方便让球员把注意力放在步伐上。
那么,对于管理而言,有什么是永恒的和易变的吗?
易变的很多,比如各种管理工具、组织理论的层出不穷。这些方法和理念的改变都是在让从事管理的人更加接近于这项工作的本质,即如何让人在工作中得到满足感和幸福感。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关于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距离问题。
用一个流行的短语来说,管理始终都是在沿着“激活个体”的方向发展。但是,“激活个体”并非一个精确的描述。“个体”是一个相对模糊的人的概念,究竟是个体的什么是管理者最需要的呢?而个体需要用什么来换取满足感和幸福感呢?
有一个理论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那就是“开放式创新”。野中郁次郎对这个理念推崇备至,因为他发现这是解放被束缚的知识的最好方法。知识可以留存于一个人的经验里,也可以抽象成一个组织的经验、一个社会的经验。对于组织经验来说,个体显然就不是激活的主要目标,甚至不是目的。只有整个组织出现联动的开放和分享时,创新才会浮出水面。
在看板管理中,个体被激活的依据也是有明确的知识引导在前,员工可以清晰看到哪里出现了问题,再根据自身经验进行现场调整。
如果不能看到“知识”是比“个体”更深层的主体的话,就难言幸福感和满足感。典型的莫过于那些常见的丰厚物质激励,低创新精神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激活的仅仅是人性中物欲的一面,却没有知识创造带来的满足感。
人们在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是因为知识的连接。但这种连接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具有多重性。每个人就像一个知识的hub,本身就是一个不同经验的集合体。这些经验中有关于专业的,也有关于非专业的。
我采访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生活工作化,工作生活化”。这是经验进行不同层面交互的结果,也是乐趣。
管理要一直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营造一个实时在线场域,其中的人不再被局限在某个带有符号特征的场所里,而是将随心所欲的工作和随心所欲的生活高度融合。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首先承认两个概念的合法性:个人公司和平台公司。
管理不断变革着,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管理动作的变化。但其使命并没有变化,即通过工作为人带来满足感和幸福感。或者说,这些正是管理变革的目的。
海德格尔很喜欢荷尔德林的诗,“人,充满劳绩,但仍诗意的栖居”。荷尔德林认为,劳动是让人向大地充分回归的介质。所谓诗意,就是纯净的自由。